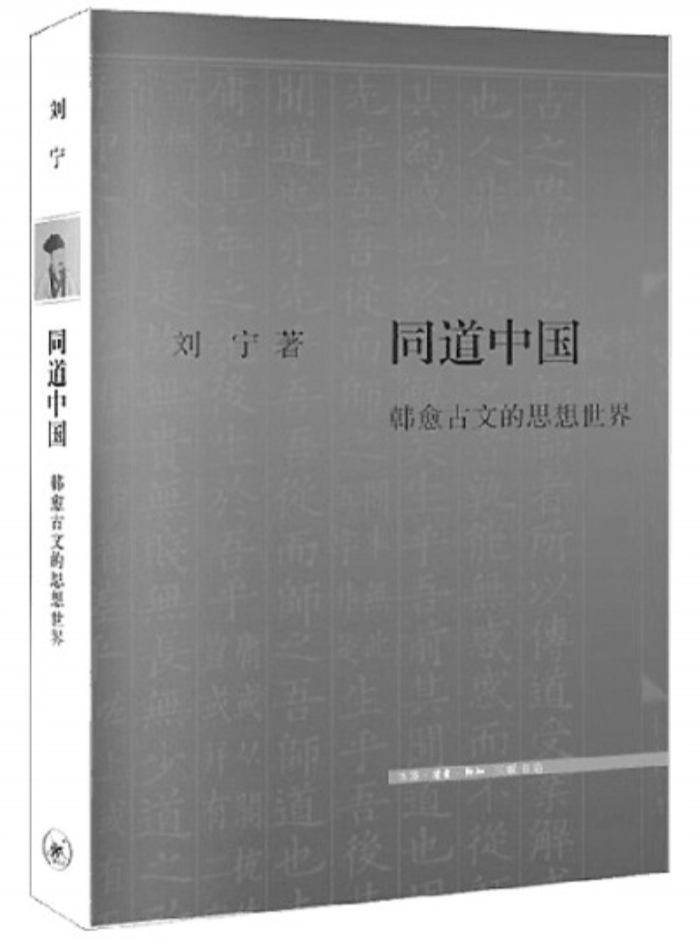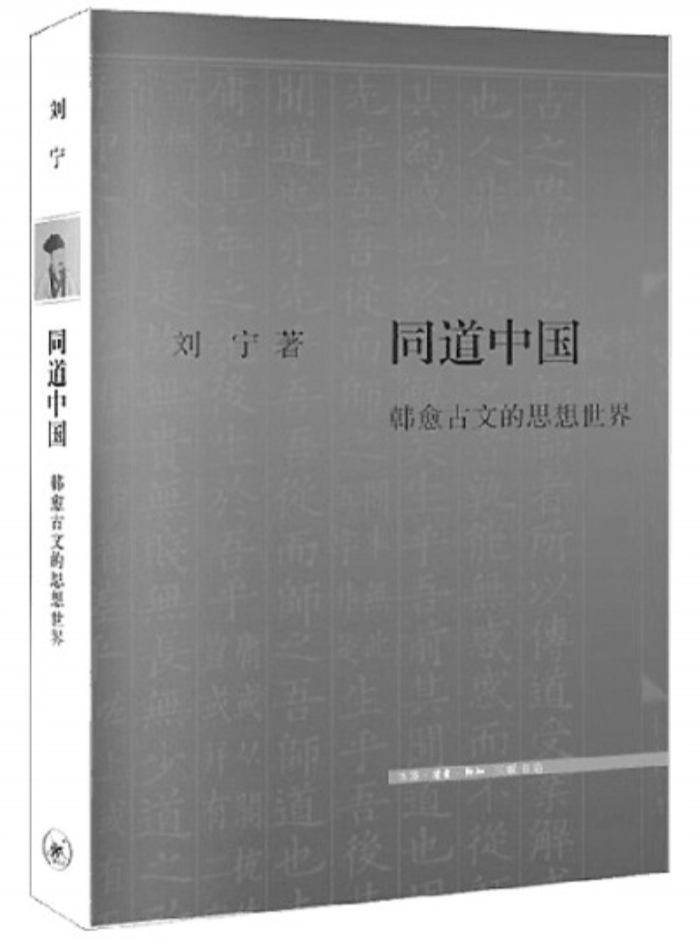
《同道中國:韓愈古文的思想世界》 劉 寧 著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
中評社北京5月4日電/據光明日報報導,韓愈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,在文章史上,他是深受推崇的古文宗師,是唐宋八大家之首。北宋詩文大家歐陽修景仰韓愈,在談及當時士人追慕韓愈的盛況時曾雲:“學者非韓不學。”蘇軾在《潮州韓文公廟碑》中,稱韓愈“匹夫而為百世師,一言而為天下法”。在他看來,韓愈以古文為天下立法,是文章宗師,更是精神的立法者。如此尊崇的評價該如何理解?韓愈古文有著怎樣的獨特之處,為什麼能在中國歷史上影響千載?
筆者近日出版的《同道中國:韓愈古文的思想世界》一書,嘗試對這些問題作出自己的解答。
中唐時局與儒學普遍性重建
要瞭解一個人物,需瞭解其所處的時代。韓愈所處的中唐,是中國歷史上極為特殊的時期。安史之亂打破了唐王朝的和平安定,使社會陷入兵連禍結、經濟凋敝、財政窘迫、民生動蕩的種種危機之中。彼時,作為中華文明精神內核之一的儒學思想,也遭遇了危機。
韓愈及其同時代的有識之士,都對時代困局深感憂慮。有的人認為社會矛盾叢生,是由於制度不立、法治不明,主張加強制度建設。如杜佑編纂二百卷《通典》,匯編歷代制度施設,期望為當時的社會治理提供參考。杜佑和柳宗元等人還提出要探索“理道”,即治理之道。但是,制度並非萬能,韓愈友人張籍感慨:“今天下資於生者,咸備聖人之器用,至於人情,則溺乎異學,而不由乎聖人之道,使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朋友之義沉於世,而邦家繼亂,固仁人之所痛也。”這就指出,時人雖然遵循著聖人設定的禮儀制度,但內心已經不信聖人之道,人倫道德的衰敗是邦家繼亂的根本。
中唐儒學所面臨的危機,突出的體現是忠孝觀念在維繫人心上日趨乏力。唐王朝作為統一的王朝,其賴以維繫的精神力量主要來自儒家的忠道與孝道。這是漢代在統一王朝格局下所確立的安邦之道。安史之亂後,藩鎮叛亂頻仍,令忠道無比脆弱。隨著科舉制推行,為官之人常遠走他鄉赴任,令孝道的踐行也面臨挑戰。在士人生活中,孝親與仕宦之間的矛盾日益顯著。韓愈《送楊少尹序》曰:“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,罷則無所於歸。”因宦而游,以官為家,這種現象的流行必然帶來社會對人倫的重新認識。人們不得不在親情之外,與社會成員建立更廣泛的聯繫。朋友之情、同僚之情的意義凸顯出來。此時,忠孝凝聚力的減弱,也襯托出佛教教義的區別。佛教主張眾生平等,突破家族血緣、身份地位等種種現實的束縛,體現出普遍性的關懷。加之社會動蕩,百姓尋求避世與內心安寧,使得佛教影響力日盛。儒學如果不能重建其普遍性價值,就很難與佛教的影響力抗衡。這是中唐儒學面對的重大挑戰。
韓愈積極地回應了這個挑戰,其復興儒學的綱領性篇章《原道》,開篇即提出“博愛之謂仁”。《原道》全篇,也流露著儒學為“天下公言”的氣象。韓愈提出,聖人的“博愛之仁”,就是關注所有人的人生日常,為所有人建構一整套安頓身心的禮儀制度,“其為道易明,而其為教易行也”。這讓作為“天下公言”的儒道,呈現出強烈的普遍性關懷。對於倡導兼愛之論的墨子,韓愈並未如孟子般拒斥,其《讀墨子》認為孔子的泛愛博施與墨子的兼愛,彼此可相為用。如此的“孔墨相用”,表露了韓愈追求儒學普遍性的強烈心聲。韓愈認為,當儒家倫理成為絕對信念和內在責任時,對它的踐行就不再受時局左右,而成為士君子自我實現的內在追求,成為人之為人的絕對意義的體現。在《原毀》中,他談到古之君子以聖人為法的原因,在於“‘彼,人也;予,人也。彼能是,而我乃不能是?’早夜以思,去其不如舜者,就其如舜者。”他認為,對儒家倫理的追求,應該是基於人之為人的價值需要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,儒學成為更具普遍性的精神價值。
進一步梳理,可發現,韓愈對儒學普遍性的追求,集中體現於對“博愛”與“自強”理念的提倡。其《原毀》雲:“古之君子,其責己也重以周,其待人也輕以約。重以周,故不怠;輕以約,故人樂為善。”君子要對自己嚴格要求,對人則寬厚以待。前者是君子自強不息,後者則是寬仁博愛。儒家有追求“為己”之學的傳統,韓愈則將“為己”與“博愛”緊密地結合起來。他推崇自守道德並且守道不遷的精神高標,在《伯夷頌》中稱頌伯夷“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”,同時他強調對待他人不應求全責備,而應以尊重和鼓勵為本。自強與博愛的融合,為儒學樹立了新境界,對士人產生了重要影響。
弘揚開放之師道
韓愈大力弘揚師道,但他並不是對儒家尊師傳統進行簡單接續,而是著力提倡更加開放自主的從師之道。
《師說》開篇雲:“師者,所以傳道、受業、解惑者也。”這裡“傳道”被置於首位,強調“道”之於“師”的重要意義。其後的“受業”,不應誤為“授業”。“傳道、受業、解惑”三者,是基於學生的視角立論,即對於學生來講,老師是讓他傳承先聖之道、接受學業、解決疑惑的人。《師說》不是一篇直白宣講教師作用的“教師論”,而是處處從學生的立場著眼,闡述為學者當如何擇師、如何堅定從師之志的“學習論”。它要通過激發學者的向道、向善之志,來鼓勵其從師而學。韓愈認為,唯自尊者能尊師,衹有學者內心有積極主動的從師向善之志,才能真正做到尊師。
尊師是儒家的傳統,然而在韓愈之前,儒家比較強調師嚴道尊,強調老師對學生的約束與管教,以及學生對老師的遵從。《荀子》雲:“禮者,所以正身也;師者,所以正禮也。”意即老師要對學生進行管教,體現了禮對人的約束。《呂氏春秋》談到學生敬奉師長:“必恭敬,和顔色,審辭令。疾趨翔,必嚴肅。此所以尊師也。”《管子·弟子職》要求弟子奉事嚴師“朝益暮習,小心翼翼”。韓愈的《師說》則不強調嚴師的威儀和弟子的恭謹,而是在喚醒學者自尊、激勵其奮進中循循善誘。以自尊為本的尊師,才能突破門戶意識,建立“道之所存、師之所存”的師生關係。不僅如此,韓愈還提出“無貴無賤,無長無少”,師生關係應超越現實身份、地位、處境的種種羈絆,成為相互砥礪的精神同道。《師說》結尾處,還特別闡發了“聖人無常師”之理:“孔子師郯子、萇弘、師襄、老聃。郯子之徒,其賢不及孔子。孔子曰:‘三人行,則必有我師。’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,師不必賢於弟子。”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開放、最活潑的師生關係。
韓愈對新的師生關係的倡導,不僅體現在文章中,也體現在收招後學、獎掖後進等方面。彼時,社會上有“韓門弟子”的說法(李肇《唐國史補》)。韓愈和韓門弟子,多數都沒有發生在學校裡的直接師生關係,更不是科舉中的“座主”與“門生”。他們成為師生,是基於共同的求道之志。用一般的標準來看,韓愈與韓門弟子的關係頗為鬆散多元,亦師亦友。錢基博《韓愈志》記韓門弟子主要有十人:張籍、李翱、皇甫湜、沈亞之、孫樵、孟郊、賈島、盧仝、劉叉、李賀。張清華《韓愈大傳》認為韓愈有四友:孟郊、李觀、樊宗師、歐陽詹;韓門弟子有八人:張籍、李翱、皇甫湜、沈亞之、賈島、李賀、盧仝、劉叉。其他研究者還有不同的統計結果,如劉海峰《韓門弟子與中唐科舉》提出韓門弟子有三十七人。事實上,這個名單不可能完全統一,韓愈所建立的師生關係就是“道之所存,師之所存”的開放關係。韓愈所提倡的師道,強調學生的自尊自重,強調超越門戶意識的師生以道相合,為儒家的尊師傳統開創出新的格局與氣象。
創造“明道”之古文
韓愈是影響千年的古文宗師。從南宋到明清,古文的創作與傳播持續深入,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古文經典譜系。韓愈作為八大家之首,其影響更是深入人心。對於古文傳統的建構,韓愈做出了開鑿鴻蒙、發凡起例的創造性貢獻。
韓愈創作的“古文”,與“時文”“今文”相對,後者主要是指自八代以來,直到唐朝還十分流行的駢文。蘇軾稱韓愈“文起八代之衰”(《潮州韓文公廟碑》),就是指韓愈不再因循八代文章的舊路,而是以極大的創造力,建構了文章新體格與新語言。在文章的體制結構上,他圍繞擬聖精神塑造古文的靈魂,讓古文擺脫中古“家言”的舊格局,成為希聖、希賢主體精神的表達。他圍繞定名追求,改造儒家的正名邏輯,為古文建構獨特的議論方式。韓愈認為古文具有修辭明道的深刻意義,創作古文既是為文,又是在精神上不斷涵養磨煉以優入聖域的過程。主體精神充盈的古文作者,在創作中會有充沛的氣勢和旺盛的精神力量,其行文必然“氣盛言宜”。觀覽韓文氣勢,不是一味揮灑傾瀉,而是濃烈中有沉鬱、奔放中有低回。北宋蘇洵說:“韓子之文,如長江大河,渾浩流轉,魚黿蛟龍,萬怪惶惑,而抑遏蔽掩,不使自露,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,蒼然之色,亦自畏避,不敢迫視。”(《上歐陽內翰第一書》)韓文如長江大河,奔騰萬里而又深沉博大。讀韓文既要感受其汹湧澎湃,又要領略其深沉浩瀚。
韓愈古文的“造語”成就十分突出,他以“務反近體”的激進追求,實現了駢散的對抗性融合,由此創造出極為獨特也極富生命力的新語言。他創造的許多詞語、詞組,都膾炙人口,成為人們長期使用的成語,例如地大物博、含英咀華、種學績文、去故就新、閎中肆外、雷厲風行、再接再厲、同工異曲、不平則鳴、垂頭喪氣、語言無味、面目可憎、曲盡其妙、顛倒是非等等。這些只是韓文所造新語的很小一部分,又如“業精於勤荒於嬉,行成於思毀於隨”“弟子不必不如師,師不必賢於弟子”“聞道有先後,術業有專攻”等等表達,也傳誦不絕。
韓愈創作古文,追求“文以明道”“文道並重”。韓愈對“文”的意義給予了充分的重視,其《答陳生師錫書》雲:“愈之志在古道,又甚好其言辭。”在《答李圖南秀才書》中說:“然愈之所志於古者,不惟其辭之好,好其道焉爾。”“文”在韓愈看來,表達了古文作者的主體自覺,展現了精神修養的豐富內涵,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。
韓愈所創造的古文傳統,不是單純的文章傳統,而是內涵豐富的精神文化傳統。宋代以下,士人代代誦習以韓文為代表的古文,深切體會儒家倫理作為絕對信念和內在責任的意義,在古文的化育下,成為彼此同道相應的精神共同體。這個“同道共同體”立足於對絕對信念的信仰、對內在責任的承當,其同道情懷無需依賴親情的聯結和禮法的牽系。韓愈《師說》對此有最好的表達:“是故無貴無賤,無長無少,道之所存,師之所存。”這既是表達韓愈所理解的師生關係,也是其所建構的“同道共同體”的真實寫照。這個“同道共同體”在千年時間裡,一直是士人的理想追求,為新儒學奠定了最廣大的社會基礎。對中國文化的鮮明自覺,是這個“同道共同體”的核心。涵育“同道中國”是韓愈古文對中華文明的重要貢獻。
費孝通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關注“鄉土中國”且終生都在思考,中國如何從“鄉土”走向世界。這一思索,與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同心同意。韓愈古文所涵育的“同道中國”的精神傳統,正是傳統中國走出“鄉土”社會的伏筆,亦是構建新型社會關係的努力,認識這一努力的意義,才能發現近代以來中國走向世界的歷程,其實並不完全是從“鄉土”、從“家”起步,曾經伴隨古文的傳習而影響千年的“同道中國”理想,為這個征程做了準備。
韓文所呈現的擬聖精神、定名追求、絕對信念、勇毅激情,以及奮進求變的態度,隨著韓文在千年間的代代傳誦,深深地鐫刻在中國人的文化氣質之中。在20世紀以來的時代環境中,“同道中國”的精神遺產,並非那麼容易被拋棄,它所特有的精神品質,還在潛移默化地產生影響。面向世界建設中國文化的未來,離不開對“同道中國”的再度思考。理解中國,既要看到“鄉土中國”,也要看到“同道中國”。
綜上所述,韓愈是文章宗師、思想巨人,他以重振儒學、弘揚師道和創造古文的卓越貢獻,深刻回應了中華文明曾面臨危機時士人應如何應對挑戰。其古文所涵育的“同道中國”思想,為中華文明探索了超越家族血緣、身份門第的更具普遍性的發展之路。伴隨古文的千年傳習,“同道中國”理想深刻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有識之士。韓愈對推動中華文明的創新,作出了自己的貢獻。
(作者:劉 寧,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、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)